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聚焦18世纪法国的图书出版业,在各种地下出版物中,分析了色情文学、乌托邦文学和诽谤文学三种号称是“哲学书”的文学作品,并对当时最为畅销的三种著作的文本进行分析。这些文学作品充斥着对等级制、君主制以及这些基本制度下各种现象的嘲讽,那些以色情与诽谤为主题的民间传说解构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剥去了皇权的神圣性,从根本上抨击了波旁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从而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准备。本文摘自该书第一章,澎湃新闻经上海教育出版社授权发布。

当刽子手在巴黎正义宫前院公开撕毁和焚烧违禁书时,他是在赞颂印刷文字的威力。但是,他往往毁掉的是样书,而地方行政官们手中掌握着原本——他们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随意举火烧书。因为明白一把大火只会促进销量,所以他们宁愿收缴禁书、监禁书商,希望动静尽量小。一项统计表明,18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局平均每年仅没收4.5部书和小册子,而且仅公开焚毁19部。
虽然这些书灰飞烟灭了,但是成千上万其他书却通过地下图书交易渠道秘密流行着。这些书给整个王国如饥似渴的读者提供了基本的非法文学食粮。目前,尚无人知晓这都是些什么书。
这批文学作品——流动商贩平常到处“遮掩着”出售的一类书——数量有多少,是什么版本?政府自己一无所知。除了某些尝试登记编目外,政府当局没有记载过那些被认为非法但从未被判定非法的图书。文学作品合法性的概念一直模糊,因为负责管理图书交易的政府机构凭空捏造出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在合法方面,该机构不仅签发各种特许证和准许证,还发放简便核准书(许可证),上面不写姓名,或者以“仅允许有声望人士阅读”字样登记。在非法方面,该机构没收盗版图书、未通过官方书商合法引进的图书、无冒犯性但未经任何准许的图书(通常是别国准许发行的进口的图书),以及触犯皇家敕令和不符检查官规定的三项标准——诋毁君主、教会或者传统道德——的图书。
甚至没人能够规定(所称)最后范畴里“坏书”的罪恶程度。而此类区别标准很有必要,因为有些书一旦被没收后可能会退还给书商,有些可能会成为把他关入巴士底狱的依据。1771至1789年期间,巴黎书商行会的官员系列登记了巴黎海关没收的所有图书书名。首先,这些书籍按三种标准进行分类,即“禁书”(要收缴或销毁)、“非经允许的书”(有时要退还给发送人)、“盗版书”(出售后利润归还原来的出版特许证持有人)。但是,随着登记条目增多,区别界限变得相互重叠、相互矛盾、杂乱混淆;最后,分类系统失去作用,变成一堆杂乱的条目,共有3544条之多,这些条目唯一的共通点是:它们都多少有非法味道。
谈到细微区别,这些官员们不能相信自己的嗅觉。因为,有谁能跟得上文学作品的出版速度?有谁能说出一部准合法书和一部轻微非法书之间的差别?运输经纪人应该具有这项能力,因为他们运送非法文学作品是要遭罚款的。然而,蓬塔尔利耶的一位经纪人,让-弗朗索瓦·皮昂承认自己未能识别违禁书。而且,当他向瑞士边境海关一位官员请求指点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无法明确告诉皮昂先生什么是禁书。总的来讲,所有反宗教、反政府、反道德的都不能进口。关于这些书有具体的禁令标准,例如盗版法国历史,《百科全书》及其他书。但是,书的质量和海关的关系不大,那是书商行会的事。”
当然,书商知道得多一些。书商预定装运,书商行会经理人原则上同皇家图书检查官一起检视装运。但是,大多数书商仅仅大致了解什么书实际流通,特别是那些经地下渠道传播的图书。文学刊物要接受检查,不允许评论违禁书,不过有时也会评论一二。甚至不能根据书名判断一本书。当然,书名页上会有许多暗示。任何书名页底部印着“国王特许批准”标准字样的书都属合法,尽管它或许是盗版。任何使用明显的假地址——“梵蒂冈资助出版”“男性生殖神出版社”“威廉·泰尔印制”——的书都无视法律。但是,这两个极端之间大有混淆的余地。书商们往往根据图书目录订购,甚至依据交易关系网上的传言购书,因此他们经常弄错书名。一些书商连字都不会写。当凡尔赛的普瓦索订购25部《诡计新编》时,他的瑞士供应商意识到他要旅游书《俄罗斯新发现》。这个瑞士人还正确解读了他说的“雷纳利尔”,指的是雷纳尔神父的《欧洲人在两印度的贸易和机构的哲学史》。不过,供应商严重贻误了里昂的弗夫·巴利泰勒发来的订单。他的订单好像只关乎无关紧要的“夏特勒画像”,而事实上指的是秽的、反教会的《夏特勒的守门人……艳史》。
这样的错误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位书商店里被发现有《艳史》,他会进监狱或被取消图书交易资格。运送书的马车夫会被罚款并强迫交出车上所有货物。买书的流动小贩会被烙上“苦役犯”(GAL)字样,戴镣铐发配去做苦工。这些惩罚确实发生过。
旧制度在其最后几年不像有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快活、宽容、放任,况且巴士底狱不是三星级宾馆。虽然不应该与旧制度和大革命前鼓动家们描绘的刑讯室混为一谈,但是它毁掉了许多从事文学者的人生——他们中不单单有作家;还有出版商与书商,不创造文学作品却使文学发生作用的专业人士。这些人在平常做生意的过程中要日复一日地区分合法书和非法书。通过研究他们在18世纪怎样对付这个难题,可以想出办法解决一个困扰了历史学家两世纪之久的问题——确认大革命前夕法国实际流传的文学作品中危险因素的问题,这样的研究路数避免了犯时代错置的错误。该方式不是从旧制度的正统性该受到什么样的威胁这样的现代观念入手,而是通过调查18世纪图书经纪人的习惯做法——他们怎样用行话交流意见、谈论图书,怎样相互间交换图书、定价、订货、包装、运输,并通过一个庞大系统进行销售,超出法律限制的范围把书传播给读者——提出识别违禁书的可能性。
鉴别违禁文学作品的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兰斯有位名叫于尔·卡赞的书商,他因为在店里出售各种禁书和有害文献而被捕并关入巴士底狱。审问这位犯人时,要他解释一个他在书信中常用的令人困惑的术语:“哲学读物”。卡赞把它解释成一个“图书交易中表示所有违禁物的习惯说法”。听说过其他术语:“煽动性图书”“药品”“苦难”。如前所述,有自己喜欢用的术语:“坏书”。印刷工使用自己行业俚语中的另一术语:“栗子”(指违禁书),“摘栗子”(指从事秘密工作)。不过,出版商和书商则喜欢一个更高层次的术语:“哲学书籍”。这个术语是他们商业密码中的一个符号,专指那些给他们带来麻烦而必须谨慎处理的图书。
最便利于研究图书交易术语的资料是纳沙泰尔出版的书信资料,该社位于法国东部与瑞士接壤边境地区纳沙泰尔公国内,是一个重要的出版商与印刷商。纳沙泰尔出版社,像几十家同样的出版社那样,需要天天应对供货满足需求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应对交流沟通方面的难题。要把装着易损未装订单页的沉重货柜经原始道路在合适的时间运到合适的地点以交付给合适的人,出版商必须弄懂所收到信函的意思;他们的客户发出订单时也必须直截了当地表明意图。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主管们从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从未见过面的书商那里收到订单,订购从未听说过的图书。书名经常不准确、拼写错误,或者难以辨认。而且,这些书时常惹祸。通过错误的渠道发送错误的图书必定会引祸上身。但是,一个人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法国文学作品和混乱的日常邮件中识别好坏呢?
出版商们依靠密码。“哲学”表示危险。开始做生意时,纳沙泰尔出版社主管们没有存放多少违禁书,也不喜欢使用交易行话。他们曾写信告诉一位书商说:“时常有一些不十分合适称为‘哲学类’的新作品出现。我们没有这类书,但是我们知道哪里有,如有要求,也可以供货。”不过,他们不久便明白“哲学”一词指的是很多客户最为看重的一部分生意。里昂的P.J.杜普兰告诉这些主管们他渴望做图书生意,“尤其是哲学类图书,好像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偏爱”。马努里从卡昂写信说:“你们有关于哲学方面的图书吗?这是我的主打书。”来自法国的信函用五花八门的语言表达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哲学作品”(贝尔福的勒利埃夫尔)、“哲学著作”(雷恩的布鲁埃)、“哲学书”(吕内维尔的奥狄阿尔)、“各种哲学书”(图尔的比约尔)。
由于业内所有人都使用这种密码,当书商们——以奥布河畔巴尔的巴特拉斯为例——发出空白订单要“你们全部最新哲学著作每种3册”时,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供应商应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书商们靠同样的假设打探信息。因此,朗格勒的卢耶尔要求:“如果你们有什么好东西、新东西、新奇的东西、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好哲学书,还请告我为盼。”里昂的小雷诺尔强调:“我经营的都是哲学书,除此以外我不要其他类的书。”供应商们被期望知道什么书属于什么种类;不论怎样,订单通常表明这一点。在一份有18种书名的订单里,小雷诺尔用十字符号标出全部“哲学”著作,并且说明这些书应该小心藏于货柜之中。这些书一共 6种:《教父马修》《夏特勒的守门人……艳史》《快乐的少女》《太太学堂》《论精神》《2440年》。这是典型的选择,范围如我们目前所知的包括色情文学和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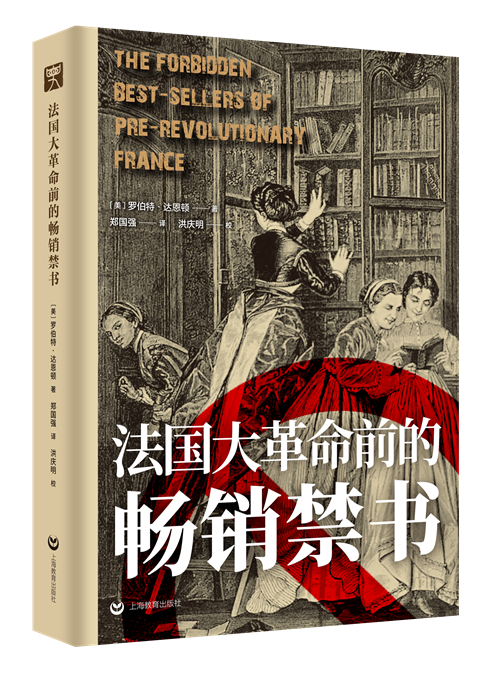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郑国强译,洪庆明校,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