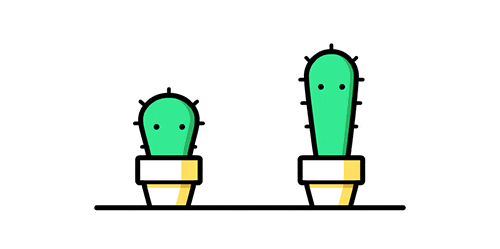在当代人的想象中,中国古代皇宫之外的女性总是顺从、压抑的,在影视作品中,她们被塑造成忙于生计的“劳动者”,或是为了争宠而勾心斗角“闺秀”。作为普通人最基础的“生活之欲”,则淹没在了历史的沟壑里。
在《中国妆束:宋时天气宋时衣》中,学者左丘萌以宋朝的女性为例,还原了她们对打扮与时尚的追求。从宫廷贵族,到士大夫阶层,再到平民百姓,从华丽冠饰,到百叠裙、直筒裤,时尚的风向总在变化,但有闲情追求是上的生活,大概就算是有滋有味的生活吧。
下文摘选自《中国妆束:宋时天气宋时衣》,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士女”文化,时尚先驱
赵宋一代立国后,朝堂政事的展开奠基于“革除五代之弊”。曾经崩坏的礼制、法度都逐步被重建,但整体又呈现出“宽仁”“忠厚”的轻松氛围。
这种较为开放的时代背景,鼓励着文人阶层从过去的颓中振起、整合,逐渐形成了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不只左右朝政,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还纵情肆意,追求着世俗声色。在如此风气之下,大众审美也总是以他们为导向。

影视剧《清平乐》
一向由士人承担的风雅,进而转移到与士人密切相关的女性群体之上——她们可能是士大夫的妻母眷属,也可能是士大夫所蓄养交游的姬妾乐伎。究其背后的原因,大概有两方:一是男性士人的儒雅风流需要知意识趣、才情不俗的女子来妆点;二是女儿家自身也希望用士族的风雅来丰富生活。
为时代所限,她们不能如男子那般建功立业,但在生活中得以处处比照士人趣味,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结社唱和,都与士人不殊。甚至可以说,她们形成了特殊的“士女”群体,呈现出男性士人官员或幕僚若生为女子时会呈现的模样。
彼时女郎的入时妆束,也总是以“士女”群体的好尚为标杆。尽管士大夫阶层或文人群体对此少有正的文字记载,但若干蛛丝马迹仍会时时在宋人笔记或词作中散逸出来。
从中得以发现,妆束呈现出了一些有别于五代宋初的新气象:种种时装都不再如往昔那般被视作浪漫的“传奇”或“传说”,而是细细融入日常生活。女性妆束同样也在“革除五代之弊”,逐渐舍弃了前朝种种浮夸的奢华奇巧,整体呈现出内敛含蓄、清雅秀美的风格。
01
民间女性也头戴华丽冠饰,效仿宫廷时尚
仁宗朝(1022—1063 年)
宋仁宗继位后,“约己以先天下”,明确表现出节俭之念。他在景祐三年(1036 年)八月下诏,对天下士庶之家的舆服式样在制度上作了详细规定。
但随后,仁宗自己就屡屡违制,常给予自己的宠妃张氏超出常规的赏赐,对她在衣饰用度上的逾越也一再包容;只有在爱妃衣装引起他人纷纷效仿时,仁宗才不得不稍加管束。
一次风波是关于张贵妃的珍珠首饰。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宫中获得一批来自广州的珍珠,仁宗与后宫妃嫔一同观赏。张贵妃颇有欲得之色,仁宗会意,将珍珠尽数赐予。众妃嫔顺势也向仁宗求取,仁宗无奈,只得令人再去市采买。一时间,京城珠价陡增。
为平抑珠价,敦促宫中不再崇尚珍珠,仁宗与爱妃谋划了一场表演:一日,恰逢宫中赏牡丹之时,张贵妃已将珍珠做成首饰,正向同辈夸耀,仁宗见状假作嫌弃道:“满头白纷纷,更没些忌讳!”张贵妃赶紧将珍珠首饰换下,仁宗这才显露高兴神色,就地取材,赐每位妃嫔各簪牡丹一朵。因宫中不再崇尚珍珠,民间自然珠价大减。
此后,张贵妃依旧寻求在衣饰时尚上出风头的机会。仍是在庆历年间,适逢上元节临近,张贵妃向在成都任职的官员文彦博示意需求新异花色的织锦,文彦博遂献上“灯笼锦”。这是一种红底上织出金色莲花与灯笼的珍异织锦。上元节时,张贵妃身穿一身灯笼锦裁就的新衣亮相,果然引得仁宗注目,文彦博也借此赢得上位机遇。
统治者自身就在不断违制,朝廷对世间服饰的次次禁令也大多收效甚微,凡是人们喜爱的,总能得以流行推广。如皇祐元年(1049 年),京城女性效法宫中时尚,流行以白角制作的宽冠长梳为头饰,甚至引来朝廷禁令和官员对民间戴用这类时尚首饰的女性大加刑责,可是百姓莫不对此嗤之以鼻,甚至编了歌谣来笑话禁令。

宋仁宗朝女性妆束形象(末春 绘)
直到嘉祐七年(1062 年)时,司马光在上疏中一针见血地提到,宫廷才是风俗的源头,百姓庶民们也总是效法权贵近幸间的流行时尚;奢侈的时风一吹,从京师的士大夫,到远方的军民,自然衣物用度都崇尚起华而不实来。
然而,无论是在宫廷还是民间,人们都在太平盛世里沉太久,奢侈享乐的大势已不能回转。虽然衣装上的奢侈风尚时盛时衰,或显或隐,但随着仁宗朝以来针对礼仪服饰的相关规制不断完善,以往贵族女性流行的广袖披衫的时装逐渐被升格成为一种礼制化服装,专用于隆重场合,不再出现于日常服饰之中。
一则宋人杜撰的神异故事,与当时时尚变迁有关——故事的主体,是讲西蜀人张俞在路过骊山温泉时,梦中与杨贵妃的一场艳遇。虽故事本身只算文人的庸俗幻想,但作者大概是为了增加可信度,特别在故事中让杨贵妃这位唐朝最大的时尚偶像关注起宋朝女性的穿戴潮流来——杨贵妃问:“今之妇人首饰衣服如何?”来者答:“多用白角为冠,金珠为饰。民间多用两川红紫。”而接下来杨贵妃取出自己的旧衣作比较,则是“长裙大袍,凤冠口衔珠翠玉翘,但金钗若今之常所用者也,他皆不同”。
故事中来者讲述的宋朝妇人时装,正对应仁宗朝的潮流——民间女性也头戴白角与金珠制作的华丽冠饰,同时效仿当时的宫廷时尚先锋张贵妃,喜爱用来自川蜀的红紫色衣料裁制衣衫。
但故事中对杨贵妃旧衣的一番描述,实际并非真正杨贵妃时代衣装的真相,而是宋人所熟知的五代妆束。在清宫旧藏的《宋宣祖后像》(宣祖后即宋朝太祖与太宗之母,主要生活在五代时期)上,便能看到所谓“广袖大袍、凤冠口衔珠翠玉翘”——这幅画的源头可能只是一帧时装,因像主身份逐渐尊崇,画经由北宋宫廷转摹添改,才多出了反映等级的珠翠凤冠和霞帔等饰物,一身时装被升格为有着严密规制的礼装。这种广袖对襟的大袖衣,在宋人眼里成为后妃命妇的常礼服或民间女性的大礼服,称作“大衣”。

宋宣祖后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绮袖时宜不甚宽,自拈刀尺勘双鸾。
锦茵拂掠春宵静,怯见飞蛾傍烛盘。
——张公庠《宫词》
孔雀罗衫窄窄裁,珠襦微露凤头鞋。
——石延年《句》其七
再来看当时士族阶层女性的流行妆束,应如即墨市博物馆藏北宋庆历四年(1044 年)金银书《妙法莲华经》写卷上的供养人一般。这是当时果州西充县抱戴里住民何子芝一家为亡母杨氏抄写制作的奉佛之物,各卷均画有杨氏领首、何子芝夫妇随后的供养人形象。婆媳二人均头戴花冠,上身罩一件松阔的直袖短衫,两襟在胸前由纽带系起,腰束曳地长裙,肩臂间绕有垂下的帔帛。
北宋至和二年(1055 年)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中有多个侍奉在座椅之侧的侍女木俑,对照来看,侍女们的穿衣模式也和供养人基本类似,内着抹胸,下系长裙,外罩直袖短衫;相较奉佛的盛装,只是少了帔帛,裙装也更短些。
这类穿搭方式实际上仍延续着唐朝女性日常衣装的组合方式,若杨贵妃真能见到,大概是不会如宋人所想象那般大感惊讶的。只是当时将上衣松敞在外、裙腰低系甚至抹胸外露的穿法,是杨贵妃不曾见过的、晚唐五代以来的新风尚。
02
小袖、百叠裙:宋朝的“中产阶级”时尚
神宗朝(1068—1085 年)
垂柳阴阴日初永,蔗浆酪粉金盘冷。
帘额低垂紫燕忙,蜜脾已满黄蜂静。
高楼睡起翠眉嚬,枕破斜红未肯匀。
玉腕半揎云碧袖,楼前知有断肠人。
——苏轼《木兰花令·四时词·夏》
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被贬官前往黄州,爱姬朝云相随同去,该词即苏轼在黄州时为朝云所作。红颜知己宽解了苏轼落魄的愁肠,至元丰六年(1083年),朝云已为苏轼诞下一子。
苏轼极高兴,写信告知友人,信中径将朝云称作“云蓝小袖者”,想必是因为友人见过朝云,却不晓其名,所以苏轼以她当日所穿的衣衫来称呼。

宋神宗朝女性妆束形象(末春 绘)
这种小袖正是当时出现的新式时装,是一种兼顾贵族与庶民审美的“折中主义”款式。 它的衣身依旧延续着宽缓的制式,袖式却颇见新意——袖根部分依旧松敞宽大,然而越向手延展便越渐收缩,至袖口处已变得颇为窄小。
之所以这般处理袖口,自是为了方便日常行动。这大概是士大夫官僚家庭中的女性吸纳民间劳动女性服装款式的创制。她们无法像养尊处优的贵族阶层女性那样完全脱离劳动,在持家生活中,时时仍有“深院无人剪刀响,应将白纻作春衣”“象床素手熨寒衣,烁烁风灯动华屋”的劳作情景,但毕竟家境较平民百姓宽裕得多,用得起多余的衣料,也有闲情在衣上加以装饰。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韩熙载夜宴图》残卷,研究者已考证其为一个较早的北宋摹本,画全不似原画应属的五代南唐背景。其中女性人物身穿宽松的对襟开衩小袖短衫衣式,已呈现出苏轼、朝云时代的流行时装风貌。推想当时摹绘的北宋画师大概不喜五代南唐的奢华穿衣方式,只是借用原本古画的构图,创作出“士大夫交游、娇姬美妾在侧”这种更迎合时世风貌的图景来。

《韩熙载夜宴图》残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百叠漪漪风皱,六铢纵纵云轻。
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苏轼《梦中赋裙带》
与北宋女性裙装关联的一个著名典故,来源于苏轼自己所记的两次神异梦境——嘉祐元年(1056 年),苏轼为参加科举答案首次出川赴京,在途经唐华清宫旧址时,梦见唐玄宗命他为杨贵妃的裙装赋诗,苏轼当即作《梦中赋裙带》诗一首,醒来便将诗记了下来。多年以后,已经为官的苏轼被贬杭州,却又梦见神宗皇帝召他入宫作文章;苏轼圆满完成任务,在出宫之际,他斜眼往相送的宫人看去,发现她的裙带上俨然是昔年自己为杨贵妃所题的诗句。
诗中所谓“百叠”,是指裙上层叠的褶皱多;“六铢”,则是以夸张的数字来形容用料极为轻薄,仅有六铢(约 60 克)重。这样的款式,显然是苏轼时代的女裙式样,不可能穿到真正的杨贵妃身上。
它大概延续着五代后唐宫廷“千褶裙”的风貌,只是逐步向下普及开来,成为士族官僚日常也能见到的流行式样“百叠裙”。
与五代时层叠裙装的雍容华贵不同,此时的轻裙碎褶是为美人的弱柳腰肢而设,因此独爱轻薄的纱罗材质。这种式样常常见于北宋词家的吟咏,“血色轻罗碎褶裙”(张先《南乡子》)、“几褶湘裙烟缕细”(晏几道《浣溪沙》)、“轻裙碎褶晓风微,弱柳腰肢稳称衣”(李之仪《写裙带》);甚至时人写菊花的层叠花瓣,也要用这种时兴的褶裙来比拟:“重重叠叠,娜袅裙千褶”(陈师道《清平乐·官样黄》)。
03
曾经贵族女性的正式服装
成为民间女性的日常
哲宗朝(1086—1100 年)
在哲宗一朝,过去士族阶层女子流行的小袖服装样式已受到逐步富裕崛起的市民阶层的青睐,迅速普及流行开来。河南白沙宋墓1号墓的壁画上对这类女衣形式多有展现。如《梳妆图》壁画中居中女子正扬举手臂戴冠,正可现出衣袖宽松的袖根部分与收得极窄小的袖口部分。对照该墓题记与地券文字可知,墓主赵大翁葬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当属没有官职功名的富裕百姓阶层。

《梳妆图》壁画(摹本)
河南白沙宋墓1号墓出土
安徽南陵铁拐宋墓出土的衣物中,恰有多件对襟短衫的实物,维持宽身阔袖的松缓样式,袖口却缩得颇小。墓主安康郡太君管氏为北宋名臣徐之母。她大约在徽宗朝崇宁年间(1102—1106 年)去世,但这些衣装并未追逐徽宗朝年轻女子流行的“时世妆束”,仍维持着她青年时代的旧样,带有一定前代的妆束风格。
此外尚需一提,北宋中期以来,以往女性流行的长披衫衣式逐渐和正装“背子”合流,成为一种仅次于大袖的正式衣物。如神宗元丰四年(1081 年)司马光为士庶制定礼仪规制的《书仪》一书中,再次提及“背子”这种衣物,女性在笄礼中便需穿用背子,服丧时也以背子作为仅次于大袖的正式衣物。
这种衣式的具体式样,大概类似管氏墓中出土的一件半袖衣,它依旧维持着五代宋初的褒博宽大式样,穿着时下摆垂及腿部;同时其袖展也进一步延长——这大概是因为原来背子是罩穿在大袖之外,随着大袖被升格为礼服,而背子作为次一等的正装,内衬的衣物变作小袖衫子,背子的袖长可以不必为袖口展开的大袖让步,于是得以进一步延长。
直到哲宗时代,背子仍具一定的正装意味。史载向太后(宋神宗皇后)在其子宋哲宗晨昏定省时,必定要穿背子;如果只穿日常服装而未及穿上背子,她就会道歉谢罪不已。有人问道:母亲见儿子,何必这般谦恭?向太后却认为,哲宗虽年幼,却是国君,即便作为母亲,也不宜用轻慢的礼仪见国君。
元祐八年(1093年)上元节,丞相吕惠卿的夫人参与宫中举办的宴会,出宫后向亲友言说宫中情形,称出席宴会的太皇太后高氏、太后向氏穿黄背子,衣无华彩;哲宗之母太妃朱氏则穿红背子,上用珍珠作为装饰。可见这时背子仍被上层当作正式衣装。
背子与日常服装的等差在同时代文物中反映得颇为清晰。如河南方城金汤寨北宋绍圣甲戌年(1094 年)范通直墓出土的石雕女像,一位双手袖于怀中的年长女性,头戴冠,小袖衫外罩穿一件袖口更宽、下摆垂及足的背子;而另一位头梳双鬟的少女,则身着对襟短衣,拦腰系一条褶裙。

石俑
北宋绍圣甲戌年(1094 年)
范通直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扬州出土的一方“宋故邵府君夫人王氏之像”线刻画像,同样将背子与衫子的等差展现得相当明确。侍奉在侧的婢女穿小袖短衫,下系褶裙;坐于椅上的主母王氏则在衣外罩了一件更为宽敞的背子。
但也是在哲宗朝,这种原被贵族女性用作正式服装的背子,正逐渐失却威仪,进一步下移成为民间女性的衣物 。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殿内保存有元祐七年(1092 年)至绍圣三年(1096 年)间绘制的壁画,下部绘有多组当时女供养人的群像,榜题均为“邑婆某氏”,应当都是较为富裕的民间女性。她们所穿的背子领口开敞,从肩部披挂而下,有的更采用近乎透明的纱罗质地裁制,透出了内穿的衫子。
在哲宗朝后期,随着背子愈加普及,甚至连底层乐伎都敢于大胆穿用。如河南登封黑山沟村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李守贵墓壁画中绘有两名乐伎,吹笙者穿浅黄色背子,拍板者穿粉色背子;山西平定姜家沟宋墓壁画中的一班乐伎更为齐整,也均穿有红或白色背子。
当时大臣张耒在上书哲宗的《衣冠篇》一文中,不满地描述了这种衣冠失等的情形——以往人们不用问,便能凭借衣冠辨认尊卑贵贱;如今上下贵贱冠服一概,哪怕略有细节不同,依旧是难以辨认身份了。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清照《一剪梅》
这首词是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新婚后的别曲之一。裳即是裙的雅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句,或解释为李清照解下因长度过长而不便的罗裳,或解释为轻挽起罗裳,自然都是为得登舟之便。不过,若是对照当时的裙装式样来看,是不必作如此曲折补笔的——裙装的基本功能,是系在外层将内衣遮盖。
而北宋中期大约在宋神宗朝以来,女性就舍弃了往昔大口开裆的宽袴加外罩襜裙的内衣搭配,在出行时选用更为轻便、如男子所穿式样的合裆直筒裤,外罩的裙也在前后增加开衩——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为了便于出行时两腿分开骑在驴上。

宋哲宗朝女性妆束形象(末春 绘)
这种裙式不再具备遮掩内衣的功能,成了一层形式化的装饰。北宋名臣司马光甚至就此大加抱怨,言称这样的服装风潮起始于汴梁城中的,士大夫家的女眷纷纷仿效,可谓伤风败俗、不知羞耻。
虽文人对这一起始于市井的时尚颇为不屑,它却在仕宦之家的女眷中迅速流行开来。
对照前引白沙宋墓壁画《梳妆图》中女子妆束来看,当时裙装也有一种在世俗流行与道德规范之间的折中穿法:在裤装之外先围系一条较短且不加装饰褶的实用裙装,用于掩盖裤装不宜外露的裤裆部分;再在外部系以装饰性的流行裙式。
后者仍是经典的褶裙式样,实物仍可举安康郡太君管氏墓出土的一例:裙腰下压极细密的褶裥,只是裙腰却大大缩短,仅足够系腰,正是时人所谓“窄窄罗裙短短襦”(文同《偶题》)。
暗减的裙腰,可将身形衬得更显细瘦,于是当时又有“芳草裙腰一尺围”(贺铸《摊破木兰花》)、“一尺裙腰瘦不禁”(贺铸《思越人》)的夸张说法。穿着这种窄裙时,需将裙腰从身后向前围系,使裙片两端于身前相接,穿着时若静立不动,则垂下的裙片恰好合围身前;若是行步向前或身姿出现起伏变化,则裙片会向身后分开,自然留出了开衩。
再来看“轻解罗裳”一句——穿一身宋朝时装的李清照,“独上兰舟”时由静转动的一瞬,使得长裙在身前“轻解”分开,原是自然而然的事。

本文节选自

《中国妆束:宋时天气宋时衣》
作者:左丘萌 / 末春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