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焦典 | 由出版社提供
近期,余华、莫言等作家参与的《我在岛屿读书2》热播。在听到经典作家声音的同时,一些青年作家的声音也逐渐展露锋芒,焦典便是其中一位。
她的《孔雀菩提》里,一种陌生感扑面而来。在城市与雨林、摩登城市与古旧传说之间,云南大地腾跃于天马行空的想象故事。中的人物虽然生长在土地上,却又某种脱离于这个严丝合缝、循规蹈矩的世界。
《孔雀菩提》是青年作家焦典的首部集,她的身上有着很多标签:她是欧阳江河、莫言的学生,作品曾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花城》《文艺报》等平台。
当卸下了这些标签,对于文学这件事本身,焦典有怎样的思考?云南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她的故事带来了什么?她又是如何理解莫言在序中所说的“巫性”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和焦典聊了聊。
✎采写 | 张文曦
✎编辑 | 程迟
“是云南选择了我”
硬核读书会:《孔雀菩提》这部集里的11个故事都发生在云南雨林,有一种特别的云南边疆特色,为什么会选择云南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
焦典:小时候在一本杂志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是讲小鸡仔的“烙印现象”,说的是小鸡第一次睁开眼看到的生物,就会被它认为是自己的母亲。云南是我的“烙印”,我睁开眼看到的是它低低的云,是它薄而脆的风,在晾晒的床单上留下了好看的形状,出生时我看到了,所以我不会再忘记。
柏拉图在《论诗的灵感》中说:“我们将不会终止我们的探索,我们所探索的终结,将来到我们出发的地点。”同理、文学同理,我们的人生也同理。走啊走,走到最后,抬眼一看,还是走回了出发的地方。我从未主动去“选择”云南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是云南选择了我,是云南带着它的气息和故事,向我走来。

《路边野餐》剧照。
硬核读书会:这种云南边疆书写的氛围感是从何而来的?是依靠实地考察还是主观想象呢?
焦典:我多么想说,这是我实地考察得到的。那个在浓密潮湿的雨林里,穿着雨靴追踪大象踪迹的人是我;那个在业已败落的山中工厂前,“咔哒”一声踩到地雷的人是我;那个在雪山前回头的人是我;那个用火焰燃尽白孔雀最后一根羽毛的人是我。但是,很可惜,不是。
其实,博士入学面试的时候,余华老师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他问我,我本人其实是生活在城里的小孩,但为什么里好多写的都是一些山里的、寨子里的故事?我告诉老师,因为我爷爷就是地质队的,我的爸爸也是,他们就是在山里、在寨子里。有些地方,他们去过;有些故事,他们见过。他们告诉了我,那些东西就像底片一样留在我的脑海里。

《路边野餐》剧照。
硬核读书会:当你写到云南的女性时,笔触尤其细腻,呈现她们的故事时也更加切肤和敏感。为什么会对家乡的女性的书写特别感兴趣?
焦典:不仅仅是对家乡的女性,其实我对女性书写都特别有热情,我也希望自己能为女性写作的事业贡献一份力。在上大学之前,我没有深入想过太多,上大学之后,我经过一些课程和书籍的洗礼,才算开了“女性视角”的这一只眼。
我开始注意到生活中其实女性有很多隐痛,这种隐痛是非常有文学性的,不是明面上的打你骂你,或者直接的虐待、歧视,而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老师、你的周围人都说你很幸福,觉得你过得很好时,你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大大的问号。更可怕的是,有时候你连这一个问号都没有冒出来过。
加上家乡这个限定后,我不得不承认,这种隐痛变得直接和强烈了。我成长起来的氛围从未让我觉得,人因为生下来的性别不同,未来的人生就会天差地别。
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做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说,他们一开始捐赠物资给云南山村里的女孩,但是发现这些东西最后都落不到她们手上,会被父母拿给家里的哥哥和弟弟。后来他们就捐赠性别偏向特别明显的东西,比如粉红色的书包、粉红色的花棉衣,可是等他们再次去到那里,发现路上都是穿着粉色棉衣的男孩们。所以,我不得不写。我没有张桂梅老师那样决绝的意志,但至少,我还能写。

《路边野餐》剧照。
留白、逃离与巫性
硬核读书会:莫言在为《孔雀菩提》一书写的序中,将你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角色)描述为“带有几分巫性”。你觉得你的人物身上是有这种巫性的吗?你又如何理解这种巫性呢?
焦典:在莫言老师说出“巫性”之前,我其实大脑的词典中没有这个词,老师说出后,我觉得概括得真好。确实,我的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有着某种“巫性”。
我觉得我不是在写“巫性”的人,而是我认为人就是有“巫性”的,因为我相信在我们严丝合缝、循规蹈矩的世界之外,确乎还有那么一个世界:那里的树也有野心勃勃的欲望;孔雀和鱼在夜晚会出来幽会,没有人会指责它们不应该相爱;那里有格格不入的丑陋动物会爱我们,毒蘑菇和失踪的人会爱我们,还有冰雹,还有野火,还有一切陡峭的事物会爱我们。

《孔雀菩提》
焦典 著
新经典文化| 新星出版社 2023-8
硬核读书会:你写的很多故事里人物最后都有逃离的行为,比如《昆虫坟场》里离开那个出租屋的脆梨,比如骑着六脚马飞走的春水。为什么会如此喜欢“逃离”的这个意象?
焦典:逃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文学的母题了,和生、死、爱、离别一样。不光是中国,像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特质就是逃离。最开始就是一批清乘坐着“五月花”号漂洋过海,逃离被压迫的地方,想去到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这个传统可以往前推到《圣经》和《出埃及记》。
而且,我最钟爱这一母题在女性话题的照射下所能折射出的光彩。比如门罗的经常书写婚姻中的女性,表现女性作为主妇的困兽之斗。像她的《伊达公主》就是一篇逃离的故事:面对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母亲,伊达选择做一个无神论者。面对让自己留在家里的父亲,伊达只身逃到了城里,再也没回去。哪怕在结婚后,伊达也在不断地逃离社会对于一个女性的规训,在身体和精神上一次又一次地逃离。
但是逃离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最经典的就是“娜拉出走后怎样”之问。面对一个整体性、结构性的困境,逃离也许真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也许我们真的不是能改变世界的伟大人物,但我们总还有逃离的权利。也许直到最后都到达不了一块属于我们的“应许之地”,但一路走过来的轨迹,也算描绘了我们灵魂自由的轮廓。

《玩偶之家》(1973)剧照。
硬核读书会:你的故事里有很多和动物有关的意象,比如大象、鳄鱼、六脚马,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是如何选择并想象这些动物在故事里发挥的作用和角色的?
焦典:大象的耳朵又大又有劲,所以真正的大象耳朵一扇就可以飞到树上、飞到云上、飞到月亮上,真正的大象会很轻盈,一点也不笨重,它生活在自己的雨林里就像鱼生活在水里,每一阵风惊起的波纹都会引起它的警觉,尾巴一摇就会消失。鳄鱼的瞳孔尖尖的,很恐怖吧,但它可是从白垩纪一直活到了现在啊,它心中的故事会像很老很老的老人一样多。至于马,很多年前我就有一匹白马,我骑着它一跃就过了澜沧。我就是这样选择并想象了它们。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硬核读书会:在读这部集的时候,作为读者我感觉到其中一些故事经常似真似幻。比如《鳄鱼慈悲》中最后在池塘里和鳄鱼相遇的老池,读完后我会想,老池是否真的变成了一只鳄鱼?还有《木兰舟》里连划船的桨都没有带走就坐上小舟远去的玉恩奶奶究竟去向何处?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种亦真亦假的结尾留白呢?
焦典: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穿梭到哪一个平行宇宙里了。我从来不觉得他们只是一些印在纸上的油墨符号,他们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存在于另一个时空里,写就是在写另一个时空里的真实生活。而宇宙会给每一种可能以可能,对吗?
一切只是概率问题,所谓的命运就是说,大概率会怎样。比如现在我坐在这里,回答着问题,但是也有千分之一的几率,我突然心血来潮站起来决定去登雪山了。那就会有千分之一个宇宙,那里面的我,正收拾着装备行囊。
所以,我写不下结局,因为在某个时空里,也许老池这个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的老地质队员,会被鳄鱼托举上岸,重新获得活着的勇气,而那位古怪又洒脱极了的奶奶,会坐着小舟一直游进太平洋,给那些海中巨兽一点颜色瞧瞧。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硬核读书会:对于那些亦真亦假的留白部分,你在写作时自己有预设一个真正的答案吗?还是自己也没有预设呢?
焦典: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宇宙都不预设答案,我又怎么敢预设某种“一定”呢。
戴着镣铐,摆脱桎梏
硬核读书会:在之前的一个采访中,你提到过“想为一切不能发声的人发声,相信有公平、自由;想去和所有的动物植物交谈,相信万物有灵,我们并不孤独”。当你书写那些“不能发声的人”的时候,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技巧?
焦典:我可能会运用一些诗歌思维的技巧,比如更多的隐喻和象征,毕竟我一直觉得,诗歌是这个时代最后的秘密。

《路边野餐》剧照。
硬核读书会:你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取了莫言老师的博士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不断地接触到很多像毕飞宇、欧阳江河等当代作家。读了如此多前辈的文学作品之后,你在写作中如何去逃离他人视角的桎梏和套路呢?
焦典:很巧,上周在南京的新书分享会上,叶子老师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觉得我的作品,一眼看上去,其实看不太出来是受了谁的作品的影响、最近在读什么书。
如果是初学的写作者,我觉得不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写就好了,只要写出来的是好的就行,管它是不是太像谁。但如果是真的想在写作上走得比较远的话,那肯定就要去寻找自己的声音了。那我就分享当时毕飞宇老师教我的一句话——“别害怕,什么都写,什么风格都玩玩”,最后一定会找到自己的。

《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
硬核读书会:短篇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人物的命运,并附带自己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短篇像是“戴着镣铐跳舞”。你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探索写作的可能性?是更偏向于克制、留白,还是更偏向于张扬的写作方式呢?
焦典:我会更偏向于用克制和留白的方式,但是这种克制和留白更多的可能是叙事架构上的、情节编织上的。
当然,这可能也跟我自己写作诗歌有关,诗歌语词和逻辑链条就是会有很多的跳跃和空白。在里,我也倾向于这样去处理。因为我觉得短篇和长篇不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给你慢慢成长、慢慢探索,给你枝节丛生,蔓延延宕。它就是一个截面,快速、紧密,天然地带着紧迫感。
这不仅仅是说一种文字带来的氛围,而是短篇的写作本身——情节的安排、结构的编织、对话的俭省,在极为有限的字数内,要求你创造一方精巧的洞天。但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我还是比较喜欢张扬的、恣意的,有时候可能都让人觉得有些“过了”。我喜欢让语言汩汩流淌起来,让它自由随意地爆裂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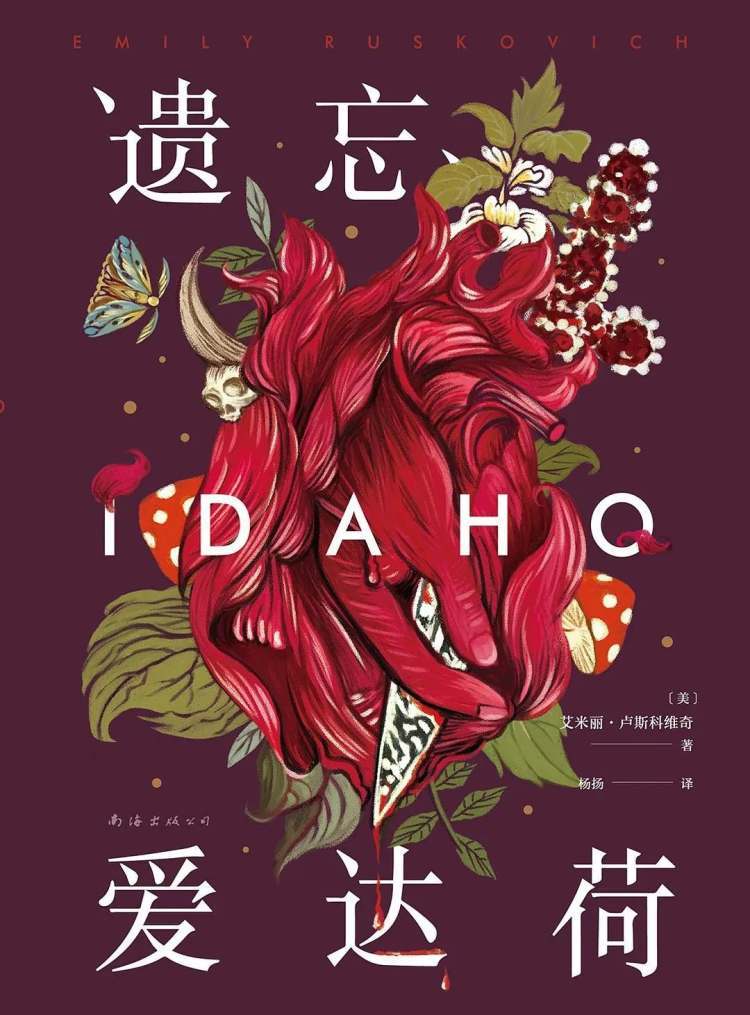
《遗忘爱达荷》
[美]艾米丽·卢斯科维奇 著
杨扬 译
新经典文化| 南海出版公司 2023-8
硬核读书会:现在在读的书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自己最喜欢的诗人和作家?
焦典:其实就是最近新出的一些作品,然后还有韩国作家金爱烂的《滔滔生活》和美国作家艾米丽·卢斯科维奇的《遗忘爱达荷》,两位也都是女作者。还有为了写论文在看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和阿多诺的《美学原理》。
我喜欢的作家和诗人还蛮多的,非要举例子的话,我比较喜欢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他的短篇《南方高速》一度让我非常震动。在一场现实到无以复加、又奇幻到无以复加的大堵车后,科塔萨尔在最后写道:“为什么深更半夜在一群陌生人的汽车中,在谁都不了解谁的人群中,在这样一个人人目视前方,也只知道目视前方的世界里,要这样向前飞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