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教授以及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最近成为焦点。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致命弱点》一文中,他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总结为三点:“一、在国内介绍和推广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西方与各国顶尖学者展开对话,同时朝着重新树立中国的历史观和时间本体论的方向努力。二、通过支持和推动宗教社会学、族群社会学以及帝国研究等领域,帮助国内社会学在研究视野和研究问题意识上从内地拓展到边疆,从边疆拓展到海外,做大国的学问,为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理论准备。三、开展对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总结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得失,在认识论层面试图寻找和建立一个能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对话,但同时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科学方。”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此。
3月24日下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专访了赵鼎新教授,在他看来,在浙江大学的这些年,“实现的要比当初设想的多”。以下为访谈正文。

赵鼎新教授 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拍摄
澎湃新闻:对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您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赵鼎新:我的学科建设思路分几个层面。
第一是招顶尖学校的、学术训练比较好的青年学者。
第二是帮助这些青年学者尽快适应中国情况,适应中国社会,然后继续能在顶尖的国内、国外杂志和出版社发文章,特别是发能在世界上产生持续性影响的西方主流大学出版社的专著。
第三是这些文章、专著在本体认识论基础上要有一定的中国视角、中国问题意识,但是同时又能让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我所说中国视角和意识不是很便宜地描述一些西方世界似乎“没有”的东西,并且标记为是中国的特殊,而是在本体伦、认识论和问题意识层面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目标,我做了很大努力。
澎湃新闻:您在浙大的一些尝试,比如鼓励青年学者投外国顶刊、长聘机制等等,按照国内高校的评价体系,会不会对他们有影响?
赵鼎新:短期内看,我们的学者是没有优势的,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浙大社会学系是个新系,人员主要是通过新的长聘体系召进来的,长聘体系有它的一套规则,青年学者成长会比较“慢”。
第二,在长聘标准上,我们不是以课题多少、文章多少和帽子多少为准则,而是鼓励青年学者去做“十年磨一剑”的学问,同时请了一批以北大、人大、清华等大学的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把关。这样在产出文章数量上肯定会低于那些做短平快研究的学者。
第三,我们招了不少研究不太容易申报国内课题的、具有一定“敏感”性议题的学者。他们不但没有课题可以申请,并且很难发表。同时,在社会学系把中国的声音打出去的长聘“压力”下,他们的文章和书籍主要是依靠外文发表。必须说明,“养”一批这样子的人非常重要。我举多年前一直反对一胎政策的学者,当时他们做的也是“敏感课题”,现在来看,幸亏有这些人顶着压力一直在发声。
澎湃新闻:您指的“中国意识”是怎样的一种视角?您认为社会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赵鼎新:中国问题意识这一议题可以从多方面来阐述。与我自己最近的思考相关的是,类似于西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古代中国比比皆是。比如清朝有一位官员去黑河地区考察,他在报告里面写道:当地发生旱涝灾害最主要的原因是森林砍伐。原来山上有很高的黑松林,二三月份天气转暖的时候,松林上端的雪融化成水流入当地50多条渠;到五六月份的时候,松林下的积雪消融又可以再一次灌溉田园。然而,当黑松林都被砍光后,洪水只发一次就没有了——一次大洪水下来会太多太涝,后续再没有雪水灌溉了就会发生旱灾。这是多么好的因果关系分析!
但是如果李约瑟给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介绍了西方的科学,并且说你们这些分析方法就是科学,中国的士大夫可能会矢口否认。这是因为科学的核心并不是基于经验观察的理性因果分析,而是控制条件下的假说检验。科学的这一片面深刻性特点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导致了不少问题,而这一方法一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问题就大了。科学家有很强的追求“常道”的倾向,但是老子却说 “道可道,非常道”。中国古代士大夫是非常理性、非常注重因果的,只不过他们不认为通过控制实验,或者各种定量方法所得出的因果关系具有任何普适性意义,所以中国古人情愿让自己的思维方式停在“勾三股四弦五”,停在“三个和尚没水吃”,而没有普遍化到勾股定理和“搭便车理论”。
西方科学的核心并不是理性逻辑分析,而是在“控制-比较-对照”下找到具有普适性的因果关系。这既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个优势,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西方科学的起点是物理学,物理学的因果关系都具有很大的普适性,于是所有学科都模仿着物理学去寻找各种“全面普适因果”。这种科学方式在少数领域成功了,但却侵害了其他领域。到了化学、生物学和某些物理学领域已经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问题,随后蔓延到社会科学,危害就更大了。可以说19-20世纪在思想层面的灾难,就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带来的“祸害”。当然,这不是说当代社会科学一无是处,也不是说我们应当抛弃理性精神,而是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西方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各种局限,并通过理性的方式试图克服和超越。
西方有很多学者其实也在反思这些问题,并且试图采用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虽然他们的想法依我看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但其间涌现出许多思想很深刻的学者。我希望也能带出这样一批中国学者。
澎湃新闻:您的教学模式中,博士生和导师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由团队来带,为什么要这样?
赵鼎新:博士生由团队来带,是为了避免学生和导师建立各种依附关系。
第一,如果一个博士生只有一个导师,导师知识面的局限就会成为学生的局限。第二,学生很有可能变成导师的“打工仔”,只能去做导师给出的课题。第三,防止了学生学生成为导师的私人“生活秘书”。第四,学生拿了导师的经费,如果受到不公正对待,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可能导致学生的忍气吞声。而在导师组下学生的钱来自系里,关系就会更平等。
这个模式也是为了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好多学生报考进来的时候对系内的教授不了解,对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也不了解。我们让学生先学习一年,熟悉情况,然后再根据兴趣选择方向和建立导师组。
澎湃新闻:您能谈谈中美社会学界的差异吗?
赵鼎新:社会学在中国是个较小的学科,而在美国是个较大的学科,美国社会学年会每年都有6000多人参加。他们研究的议题多,面广;我们研究的议题少,面窄。当年,我们组织芝加哥大学和人大合办的讲习班,找外国学者来讲课,什么议题都找得到人;而找中国学者,很多议题很难找到人。另外,与美国相比,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共同体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由此导致了专业评价考核体系的不完善。
不过话说回来,美国社会学有过度专业化和过度正确的倾向,导致有些学问越做越小,结论意义不大;中国社会学家对大议题更感兴趣,这是个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澎湃新闻:现在社会上普遍有一种“文科无用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鼎新: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看上去“最没用”,其实却是“最需要”的。如果这些基础学科弄不好,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在国际上就不可能确立一个话语体系可以用来和西方对话,在治理上就会经常犯一些历史上早就犯过的或者最简单的社会学原理就告诉你是不能做的事情;从个人层面来看,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个从思维方式到举止都看上去比较健全的人,并且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出现各种误区。
澎湃新闻:您在接触社会学的时候,本身的学识、经历已经很丰富了,这对您学习社会学有何助益?理科的学术训练对日后社会学研究有哪些影响?
赵鼎新:我的人生阅历使得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很难束缚我,而我的理科的训练又给了我“精算”的能力。如果我不懂理科,我的许多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澎湃新闻:您这些年一直在倡导“历史社会学”,组织出版了《历史与变革》集刊。您的历史社会学视角跟历史学家有很大差别,比如您的关注点在于权力-时间的张力关系。这种时间和时间性视角是怎样形成的?
赵鼎新:这个视角很早就有了,它的丰富则经历了很长时间。
第一次对“时间”有感觉,是我九岁时,突然想到如果我死了,那么应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可能是被烧成灰,可能是被埋在土里,感到很害怕。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我渐渐发觉人对时间的感觉是非线性的,每过一年,同样的时间在感受中就会变得越来越短。一年对于十岁的人来说是他以往生命的1/10,对于一百岁的人来说是1/100。年纪越大,时间就加速越快。我对时间性有了非常初步的理解。
我们从小学习到的是时间是线性的,是有终极方向的,这就是所谓的线性时间,但是线性时间有一个犹太的源头。而中国的老子则会告诉我们时间是循环的,这说的是循环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我看书多了。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后,各种关于时间性的理论都接触了。所以我对时间和时间性的认识,是在不断学习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丰富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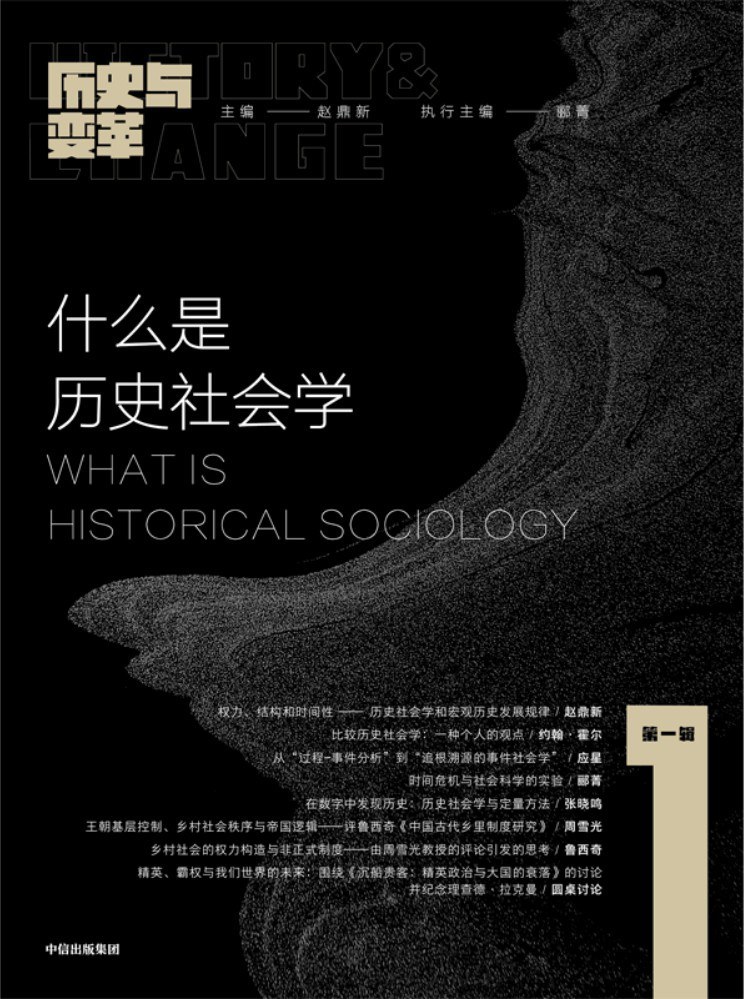
《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2月
澎湃新闻:您在《东周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运用定量分析,用平均行军距离来判断各国国力的强弱,如何想到这样的衡量方法?在研究时,如何选取合适的方法?
赵鼎新:我看当代历史学家的作品,觉得他们对春秋国家强弱的判断有一些问题,比如他们会把那些经常跟着晋国一起打仗的陈国、蔡国等也看作是春秋时期较为重要的国家。于是我就采取了一个对于历史学来说是较为另类的方法。比如对行军距离,打仗季节,哪几个国家参与了等等指标进行定量,结果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
方法的运用,其实应该都是想法在前,方法在后。应该是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决定方法,而不是用方法决定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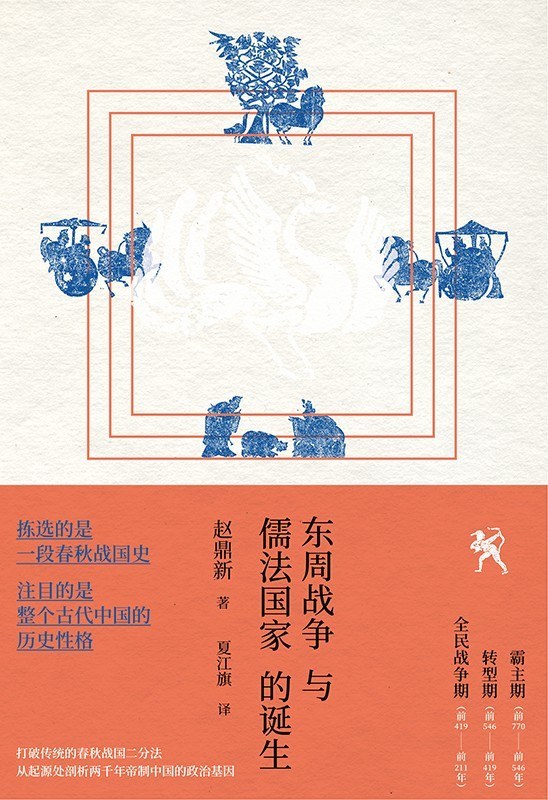
《东周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8月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现在社会学界定量研究远多于定性研究的现象?
赵鼎新:定量和定性,对于研究者来说要有机结合,什么都要懂。如果是因为不会接触人而选择做定量,或者由于数学不好而选择做定性,那就麻烦了。
从提出问题的角度看,做统计的只要把问卷中的某个问题作为因变量,其他问题作为自变量,研究就可以开始了,这主要是个技术活,因此发表速度可以很快。但定性研究则需要从历史文本中、从田野里面去找到问题。譬如做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生搞懂文本和历史场景就需要好多年,更别说要从里面提炼出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问题。
可以这么说,一个选择用统计方法做研究的青年学者5年可能已经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而做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可能仍然停留在寻找研究问题的阶段。在高度强调发表量的学术评估体系下,人家可能已经是有头衔的青年学者了,而你可能才混到助理教授。依我看,这就是现在社会学界定量研究远多于定性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澎湃新闻:您回国到浙大带领社会学系发展已经十多年了,与当时的设想相比,您觉得实现了多少?
赵鼎新:我2016年后参与组建浙大社会学系工作,2019年全职加入浙大。浙大社会学系办到这一步,虽然过程不乏艰辛曲折,我觉得实现的要比当初设想的多。在发表方面,我们系的老师在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有6部著作已经签定发表合同,后面跟上的还源源不断。这些可都是十年磨一剑的工作。就凭这一点其实就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级别了。更何况我们系的老师在多个欧美非常难以发表的顶尖杂志有发表,这在国内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此外,我们和三联出版社签约出版浙大社会学系教材系列,其中第一本书今年就可以面世。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初步确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体系。我们系建立了一支风气很正的队伍,并且人数众多,这肯定是能产生长远影响的。这些都是10年前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