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安焉,写作者。1999至2019年间一共做过19份工作,包括酒店服务员、加油工、杂志美编、女装店店主、快递员等。
2009年开始写,交替地工作和写作。2020年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获得关注,随后出版了非虚构自传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比世界晚熟》。
01
我总是那个离职很快的人
我换工作不能说完全是主动的追求。我早年换的大多数工作,还是因为遇到了我克服不了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在加油站里边,当时应该是2001年,我还没转正,只是一个编外人员,一个月是1800。转正之后还有别的一些福利奖金之类的,只要下去,很快就能转正。收入我是满意的,工作强度也不大。虽然它是三班倒,有通宵班,但是就8个小时,不存在加班。因为时间到了,下一班的人都来了,你想加也不用加。
但是运气不好,当时中石化要弄一个示范站,就把我挑去了。我是站里最年轻的,可能他觉得我个人形象也符合这个示范站的要求。因为他要拍出一套规范服务的教育片,在中石化内部去推广,所以挑了我去,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本来加油站离我家和我的夜校都非常近,两三公里以内,我骑单车就能到。但是那个示范站是在十几公里外的郊区,而且希望我们下班后不要离站,住在旁边的员工宿舍里。
其实如果我一定要干下去的话,我也可以跟领导说,我在读夜校,时间有冲突,不能下班后还要住在这里。但是我当时20岁出头,连面对领导都害羞或者害怕,更不要说谈条件。所以我选择离职,因为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到了下一份批发雪糕的工作,我也是因为性格上的一些问题做得不顺利。一个是我害怕竞争,不喜欢跟人产生摩擦。第二个是我没法跟领导、客户或同事去提要求。
我到了一个新公司,总是员工里边看起来最认真的一个人。从来不迟到早退,服从性非常强,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可能总是那个离职很快的人,因为这其实是在透支,这种损耗是没法得到补充的。另外一个同事可能像老油条一样,你叫他干,他只出一半的力去干,平时跟你谈谈条件什么的。可能看起来不负责,但是反而能干得长久,因为他没有积累那么多排解不出去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以及实际的困难,比如说夜校时间冲突这种困难。
我在学生阶段虽然也是一个害羞的人,但跟同学之间打交道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不涉及利益。但是踏入社会之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简单了。而这个时候我察觉到我其实是有讨好型人格的,当别人对我不满、有敌意,甚至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创伤性的体验。所以我宁愿让步,我不跟你争,这样能换来一些内心的平和。
02
今天我是这样一个人,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的理想主义
今天可能很多人觉得我父母的单位是一个事业单位,一听有编制,好像很好。但是在90年代的广州,对年轻人来说去台资、港资或者外资公司上班才是吸引人的。而国有单位首先工资非常低,其次编制并不是铁饭碗。因为90年代喊的口号就是打破铁饭碗。
当时很多有自信、头脑灵活的人辞掉工作下海,去做生意或者去炒股,这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将来也有可能官方的说法一变,这些人又会变成投机倒把被打倒。
那个时候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多制度方面可能不太完善。举例来说,很多单位一旦从国有变成了半民营的状态,就会有一些经济账目不清楚的情况。我母亲是会计,她的厂长希望她在账面上把这些东西做掉。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清晰地判断对错,每天惶恐不安,已经到了神经衰弱、我跟她说话她都听不到的地步。后来她也没参与,但是这样她要得罪人,可能都觉得是她要拖大家后腿,不愿意让大家多一些生存机会。在这种情理两难之间,再加上改革开放制度的发展相比于形势发展的落后,让她处在这种持续的、长达近10年的焦虑、恐慌。整个90年代她过得很糟糕。

我小时候也明显感觉到我父母对我的教育,让我在面对我的同龄人的时候差异非常大。父母跟子女说的东西,要怎么做人、怎么投入社会,说的都是不同内容。我父母从来没有什么人生规划,从来不会想要帮助我有人生规划。他们的观念还是:我们是为社会培养子女的,社会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他们不会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什么对你更有利,我来帮你实现。追求私利在他们的脑子中好像是不存在的,他们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所以1998年学校的包分配制度开始取消时,他们还觉得很纳闷,好像整个社会不负责任了。他们对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没有理解,感情上也不是十分接受。
2009年之后,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我去网上面搜索了很多资料,我去分析从小到大我妈反复跟我们说的很多口头禅,她的一些观念、做法。比如她没有任何喜欢的东西,所有菜上来全部都平均地吃一遍。她认为这是自己优秀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这是没有喜恶的表现。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喜恶的,但是她认为个人喜恶是一件错误的、有危险性的事情。她压抑了自己的喜恶,实际上也是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这些都是她的口头禅,这其实也是当时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种塑造的结果。
我父母有很多观念可能是在很扭曲的情况下接受的,但是那个观念本身是好的,比如他们相信职业无分贵贱。我也相信这些,但是我不希望是因为自己的愚昧而接受,我希望了解它是怎么影响我的。有一些观念可能有笨的一面,但是我认为它是善的,所以我仍然希望把它作为我的价值信仰。
03
一个真正能代表我这个人的事情
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可能是在我30岁之前吧。2007到2009年在南宁的女装生意经营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卷进这个生意里,需要面对很多我自己承受不了的跟同行的一些摩擦、竞争、互相的伤害甚至是暴力的冲突。当这些都反复的发生之后,我就产生了一种厌倦和逃避的心理。
上午在店里面,虽然我要守着,但是中午饭之前可能一个顾客都没有进门,没有什么人早上出来逛街,我其实是有时间去读一些东西,当时我可能就读了这个书。

▲ 当时胡安焉在南宁一家商场开的女装店
它表现的就是一种孩童一样的单纯天真,跟成人世界之间的种种的格格不入。霍尔顿他老是见到一个人就说对方假模假式,他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虚伪的一个世界,有一套成人世界的规则决定你要怎么待人处事,但都不是他们真实内心的想法。虽然霍尔顿的情况跟我的情况原因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打动我的。一个小孩从学校逃到家,逃回纽约,他其实也是一路在逃、一路对环境的不适应。
《麦田里的守望者》可能是第一部最打动我的,它可能也是我选择开始写作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写得很好,我希望也做这样的事情。
一开始的阅读都是随机的,我当时读了很多,但有些是读不明白的。后来我发现“迷惘的一代”特别能够读进去,包括塞林格、海明威、理查德·耶茨、杜鲁门·卡波特这一类作家。因为他们写的都是比较现实的故事,整个思想观念方面跟我当时身处的社会环境挺有共鸣的。
“迷惘的一代”他们描写人的一种幻灭感,追求的不可得到。他们把自己的这种生命感受转换成一个艺术作品。不一定他们在生活中能够克服这种失落感,但是他们让这种失落感获得一种美的形式,通过这种审美的形式,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一点价值。
在我30岁之前,我不觉得我做过的任何事情是真正有价值的,那我希望找到一个真正能代表我这个人的事情,不像之前的那些工作,其实换谁做都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让我有一种个人价值的确认感。在我有限的选项里边,写作是成本最低的,不需要采购什么器材,也不需要报什么班去学习,我只要拿起笔就能写。
刚开始写作的头两年,写的比较接近于像卡佛和塞林格的那种故事,素材很多还是取材自我之前的人生经历,比如说1999年在酒店里面做服务员的经历,我也用它作为素材写过一篇。一个很难处理的经验,通过的形式去创作它,它就获得了一个审美的形式。很难概括它这个作用是怎么产生的,但是总会觉得这段经历有了一个归宿,否则它总是一个负面的、让我难以面对的东西。但是你处理过了它之后,相对会好一点。
04
海水退去之后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强烈的解释的冲动,我父母也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我们是很在乎别人眼光的。有时候我意识到了,我就压制一下,但是它也成为一种动力。恰好黑蓝文学公号邀请我写一个专栏,我就借这个机会把《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里边不方便深入的那些我的精神方面的内容,总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怎么会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一个自我梳理深入写了一遍。从2021年底开始写,到2022年8月结束,这些写作最后也签了出版,书名叫做《我比世界晚熟》。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困惑还是来自外部的。如果地球上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任何困惑都不会有。我的所有心理问题都是人际带来的。
去年我的书出版之后,受到了很多关注和褒美。在2020年之前不会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来问我问题,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愿意听。有很多网上的人说,这个快递小哥好通透。但他们心里可能以为这个快递小哥25岁,他不知道我今年已经44了,我送快递的时候已经40了。
在这种状态下我很难回答我还有什么困惑。可能过了三年或者五年之后,我能更看清楚,我现在这种短暂的浑浊状态之后、这个海水退去之后,我现在可能意识不到的问题在哪里。但绝对不通透。

策划、采访|CH、张畅
执行导演、摄影|房子、Chaos、大凯
剪辑|Chaos
设计|乔四九
鸣谢|胡杨文化编辑杨子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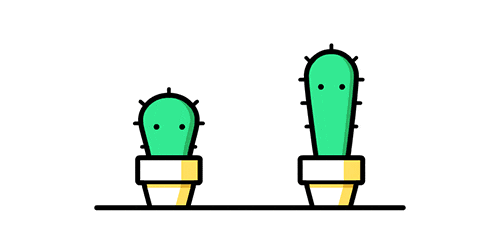
新版微信修改了公号推送规则,不再以时间排序,而是根据每位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在这种规则下,读书君和各位的见面会变得有点“扑朔迷离”。
数据大潮中,如果你还在追求个性,期待阅读真正有品味有内涵的内容,希望你能将读书君列入你的“星标”,以免我们在人海茫茫中擦身而过。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