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口秀”这个起源于西方国家的艺术舶来品,在实现“本土化”的进程中并不顺利。它几次遭遇“毁灭性打击”,而后又死里逃生。
10年前,“脱口秀”是一片蓝海,许多人投身其中,随后“笑果”这艘巨轮诞生,一路乘风破浪。
短暂辉煌过后,“HOUSE事件”,让一切回归原点。
如今,“失业”的脱口秀演员纷纷开始“再就业”:
李诞投身直播带货卖起了穿戴甲;徐志胜剪掉了刘海,进军演艺圈成为演员;李雪琴在春节档“热辣滚烫”,有网络传言称,她的工作室已成功签约庞博;童漠男以“文学策划”的姿态加盟电影《年会不能停!》……
更多的人,没有消息已经很久了,像是没出现过。
巨轮仿佛从未停下,船上的人都欣赏到了远方的风景,有人收获了很多,有人已遗忘为什么出发。


来吧,朋友,开篇先说一个有些“敏感”的人物,周立波。在中国脱口秀发展史上,这是一个理应提到的名字。
遇见脱口秀之前,他的人生一塌糊涂。
过去他在上海滑稽团当演员,因为鬼点子多、善于临场发挥,一度被剧团视为“台柱子”。1990年,周立波23岁,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两人爱得火热,不料却遭到了女方父亲的强烈反对,双方起了冲突,他一气之下挥拳打瞎了对方的眼睛,周立波因此被判故意伤人罪,入狱205天。
2006年,好大哥关栋天找到周立波,问他想不想重回舞台,做一档像香港地区“栋笃笑”一样的节目。原本这种表演形式叫“stand-up comedy”,即单口喜剧,后来也被广泛称为“脱口秀”。
实际上,最初的脱口秀节目并非如今这般模样。上世纪九十年代,“talk show”的概念刚刚进入中国内地,更多被视为谈话节目,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就是其中典型且成功的“案例”。
可那不适合周立波,关栋天想做一档更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新式喜剧,几个月之后,二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海派清口”。

周立波
“海派清口”的首场演出就大获成功,往后3年,周立波一路高歌猛进,巅峰时期舆论甚至将他与郭德纲对比,以“南周北郭”形容二人在喜剧界的地位。这理应是同行惺惺相惜、互帮互助的故事,不想周立波口无遮拦,在谈及是否会和郭德纲合作时,他调侃道:“一个吃大蒜的怎么可以和一个喝咖啡的在一起呢?”
“咖啡”与“大蒜”的言论迅速发酵,将双方当事人推上风口浪尖。几天后,周立波在演出中将争议写成段子:“这几句话你就生气了?说明你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开开玩笑的呀,有什么啦?”不想矛盾再次升级,舆论在“艺术的冒犯”和“高姿态的挑衅”间剧烈摇摆。争吵群殴了周立波,却也成就了他。
2010年,随着周立波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一档名为《壹周·立波秀》的脱口秀节目登陆上海东方卫视。前期节目分为周立波个人脱口秀表演和明星访谈两个部分,后来又增设了“立波梦话”环节,笑侃年度热点社会事件和人物,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北京的房地产、银行的贷款、上涨的油价以及领导的屁话——那是一个冒犯不讲“边界”的草莽时代。
言论尺度之大,大到在如今的互联网语境内,我甚至不敢以“外部引用”的形式到本文举例说明。就连周立波本人在“梦话”开始前,都要强调一句:“以下新闻内容是由周立波所扮演的周立波个人观点,与周立波本人无关”。

《壹周·立波秀》收视一路飘红,到了2012年,周立波已经成为国内最知名、身价最高的脱口秀演员,没有之一。
鱼养肥了,鱼塘也得扩建。为了留住周立波,东方卫视邀请他参与了几档综艺节目,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然而只有“曝光”是不够的,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周立波提出要“涨薪”,节目组有点犹豫,不想浙江卫视见缝插针,以超高片酬“邀请”周立波到自家节目做导师,没有任何犹豫,周立波转身离开,顺便还带走了《壹周·立波秀》。
痛失王牌,东方卫视满心怨怼,盘算着要弄出一档新节目PK“立波秀”。领导找来叶烽,第一届《加油!好男儿》的总导演,台里人尽皆知的“狂士”、正义的化身,曾在下班路上暴揍过一位插队打车的男士,后来被告知挨打的那位其实是副台长的儿子。

叶烽
那段时间,叶烽恰好向台里提出要做一档全新的脱口秀节目,双方一拍即合,《今晚80后脱口秀》上线。
这可以被视为中国观众认识“脱口秀”的起点,具有深刻且重大的意义,但它不是全部,平行时空里还有另外的故事。
在“今晚80后”开播的同一年,一位名叫黄西,手握抑制癌症基因专利的生化博士,决定从美国回到中国。算上求学的日子,彼时的他已经在异国生活了近20年。
2002年,黄西开始接触脱口秀,7年后,他登上有“喜剧奥斯卡”之称的《大卫・莱特曼秀》舞台,而后受邀参加美国电视记者年会,在白宫进行一场15分钟的脱口秀表演。
作为当天唯一受邀登台的中国喜剧演员,黄西的表现让所有人惊叹。他用脱口秀讽刺了美国的、法律与社会矛盾,以及时任美国副拜登:“我读过你的自传,今天见到你,我觉得书比本人好的多。”他也没有“放过”奥巴马:“一个亲手发动两场的人,诺贝尔居然还给他颁发了和平奖。”

黄西
那夜黄西一战成名,表演的视频通过互联网从大洋彼岸传到中国,他的名字成为“单口喜剧”华人圈里如同“神”一般的存在。
黄西的成功激励了许多当时还在“地下”说脱口秀的人,其中就包括了日后《吐槽大会》的编剧梁海源、程璐,二人还曾到深圳书城排队等候黄西签售自传。
到了2013年,黄西带着全家搬回中国,并入职央视主持《是真的吗?》。在节目中,他会先表演几分钟的脱口秀,然后针对网上的传言提问“是真的吗?我不信”,再通过现场实验求证真假。
那是“脱口秀”在主流舞台的又一次尝试,在此之前,央视多数的脱口秀节目都和《实话实说》差不多:一群人围坐在桌子旁,就当下热点话题发表观点,时代的进步让每个人的表达欲爆棚,可那都不是喜剧。
黄西的出现让中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清晰看见“stand-up comedy”的真实样子,新潮,也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和线下表演不同,电视台脱口秀无法使用连贯的段子,因为观众不可能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15分钟,听你讲完一个长笑话,然后为结尾的call back欢呼。段子要短,要一秒戳中笑点,否则就会冷场。(call back,脱口秀术语,反复或扣题,指在段子中提到前面讲过的一个段子。)
可以预料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观众都无法接受、理解黄西略带美式幽默风格的段子,最初录制节目时,黄西经常会在前排观众的脸上看到“同情”的笑容,那样子仿佛在说:
这里是不是应该笑一下?笑一笑吧,不然太尴尬了。

黄西主持《是真的吗?》

在黄西尝试用《是真的吗?》逗笑观众的时候,《今晚80后脱口秀》的收视率已经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相亲节目《非诚勿扰》。
两档电视节目的顺利播出,让国内脱口秀演员看到了希望,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呼:原来在中国还有这么多人说单口喜剧!
就像是忽然找到了勇气,那段时间,各个城市里出现了很多脱口秀俱乐部,圈子里忽然热闹起来。

王自健《今晚80后脱口秀》
后来,黄西本人也创立了“笑坊”俱乐部,期间还曾收到过李诞的投稿,但没有被采用。当时李诞在段子里写:“我(指黄西)是学化学的,大家看我这张脸就知道,我曾用自己的脸做过实验。”
多年后,黄西以“选手”的身份登上《脱口秀大会》还调侃了这段经历:
“谁能想到后来李诞竟然能成为全中国最火的脱口秀演员呢?我挺感慨的,如果不是我把脱口秀引到中国,就不会有《脱口秀大会》,我今天也没有机会来参加海选,谢谢李诞老师。”

黄西作为选手参加《脱口秀大会》
2014年,叶烽决定再往前走一步。想让一个行业壮大起来,仅凭一档节目是远远不够的,他想成立一间公司,把中国的脱口秀演员、编剧都召集在一起。
叶烽先去找了王自健,结果王自健告诉他,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录节目可以,合伙开公司就算了,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之后他又去找了李诞和王建国,前者答应入伙,后者向往自由,决定留在公司继续做编剧。
这一年春天,李诞、叶烽联合其他两位伙伴成立“笑果文化”,没人可以预料,就是这样一间规模不过二十几人的小公司,仅耗时3年,就变成了行业领航者。

“笑果”成立时,国内全职脱口秀演员不超过50人,“石老板”石介甫算一个。
石介甫原本是一位金融白领,在爱上“单口喜剧”的第四个年头,他辞掉了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决定用手头所有积蓄为梦想买单。
这几乎是一个“背叛祖宗”的决定,他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传统的家庭,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对于儿子最大也唯一的期待,就是安稳。
辞职后,石介甫一直不敢告诉家人真相,为了圆谎,他时常会编几个公司的段子讲给二老听,昨天那谁辞职了,今天有人迟到了——这样看来,父母算是他的第一批脱口秀观众。
同一时间段里,一位名叫周奇墨的英语老师,也辞掉了在培训机构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脱口秀演员。通过一次次线下开放麦演出,周奇墨和石介甫相识,成为朋友,后来又变成合作伙伴。

“石老板”石介甫(黑衣)和周奇墨(红衣)合作演出
“笑果”在上海成立后,迅速吸引了批脱口秀演员“南下”,北京圈子里人才流失严重,线下演出一片惨淡。
石介甫没有去上海的打算,他想留在北京弄一个可以让更多人讲开放麦的地方。他叫来周奇墨,两个人骑着电动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寻找演出场地。
有次他们跟着中介去了二环某小区,穿过幽暗甬长的胡同,来到了一间半地下室。打开门,阳光穿透窗户进入屋子,灰尘循着光束爬升,衬得房间氤氲旖旎。二人定睛一看,迷离梦幻的烟雾背后,是一排排佛龛艺术品——好家伙,太意外了!
石介甫:我觉得这地儿挺好的,要不咱租下来吧。
周奇墨:在这儿做喜剧,是不是太冒犯神明了?

周奇墨和石介甫合作演出
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周奇墨将自己比喻成“流民”,“没有故乡,没有家”,更没有钱,这几乎是所有脱口秀演员初入行的困境。
在变成“脱口秀明星”之前,多数演员的出场费都是零。绝大多数人白天需要上班,晚上才能参与线下开放麦演出。在城市的街道,他们蹬着共享单车、乘坐地铁,从城市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只为登台表演5~10分钟的脱口秀。
周奇墨记得,有一次他骑共享单车去酒吧演出,结果忘记锁车,散场时发现车被人骑走了,但计费没有停止,第二天他对着巨额账单推算,车应该已经跑上川藏线了。他忽然觉得很悲凉——自行车都看见诗和远方了,自己还没走出海淀呢。
那是一段即使倒贴钱也要去演出的日子,理想主义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现实,每个人都在为好段子欢呼,而不是为钱拼搏。
呼兰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在线下开放麦,获得全场欢呼时的心情:“激动啊,兴奋啊,那真是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一遍遍回忆。”

呼兰谈脱口秀
在所有人都一穷二白的时候,梦想与热爱是比钻石还珍贵的东西,可一旦有人发现,原来两者可以兼得时,事情就会变得格外复杂。
2017年初,《吐槽大会第一季》上线,开局即王炸。截至节目收官,全网总播放量达到13.8亿,单期播放量最高破2亿,一跃成为当年讨论度最高的综艺。之后不久,《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热浪再次翻涌,“笑果”凭借两档爆款节目火速完成两轮融资,到了2017年5月,公司估值已经突破12亿。
这是一个足以让全行业咋舌的成绩,在多数人还在苦苦求生的时候,有那么一撮人不仅找到了出路,而且还赚得盆满钵满,说“不羡慕”那太假了。
“笑果”改变了一切,它真的把梦想变成钻石了。

综艺《脱口秀大会》舞美设计
资源迅速向同一个地方靠拢,人、钱、名,“笑果”犹如一个巨大的货轮,甲板上堆满了黄金与钞票。巨轮不断加快步伐,从线上综艺,到线下演出、脱口秀训练营,它收割了整片海域。不用刻意点明,大家都看得出来,在当时想要成为“脱口秀明星”最好、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登上“笑果”的巨轮。
南方海域已经波涛汹涌,北方海面则略显平静。“笑果”广纳贤士,原本在北京定居的脱口秀演员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沪漂”,北京本土脱口秀俱乐部一片冷清。
就在“笑果”完成2轮共计2.2亿融资的2017年,石介甫拿到一笔200万的创业基金,投资方说得很直白:《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火了,脱口秀行业从“死海”变成“蓝海”了。
拿着这笔钱,石介甫成立了“单立人”,初创成员除了周奇墨,还有小鹿和“教主”刘旸,四人合称“石墨鹿教”,大家都是在线下表演时结识的伙伴。

“单立人”初创成员“石墨鹿教”:周奇墨、“石老板”石介甫、“教主”刘旸、小鹿(从左往右)
不同于大家大业的“笑果”,“单立人”更像是一个小型的乌托邦乐园。最初选择走进这里的人全都与世无争,他们只是渴望表达,渴望用喜剧疗愈自我和他人,那时石介甫最担心的不是挣不到钱,而是害怕被资本控制,限制创作。
“单立人”有很难得的“匠人精神”,这是业内公认的。在多数人都渴求在线上露脸的行业大环境里,它是极少数始终坚持线下开放麦演出、潜心钻研段子质量和表演技巧的群体。目前行业里相对知名的脱口秀演员,杨蒙恩、rock、杨笠、童漠男、徐志胜,都曾是“单立人”的签约艺人——
是的,他们后来全都跳槽去了“笑果”。
比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那些没能在“单立人”线下走红的脱口秀演员,借助“笑果”的线上综艺一夜成名,理想砸在金灿灿的舞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然后哗啦啦爆出一堆金币——那个东西真的太吸引人了。
到了“现实”向“理想”发问的环节了:舞台就摆在那,你去还是不去?

综艺《脱口秀大会》舞美设计

在外界看来,“笑果”与“单立人”之间的人员流动就是一场“抢人大战”。可当事人石老板认为,所谓“竞争”并不存在,热衷造浪的南方巨轮,理应不屑与北方海域里的一叶扁舟争流。
石介甫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浪打来了”,是在2020年。
那一年“石墨鹿教”中的小鹿参加了《奇葩说第七季》,不久后与“单立人”解约,有传言称她已加盟“米未”;“教主”刘旸同样也参加了这档节目,但反响平平,他迷失了,陷入长久的自我怀疑;周奇墨连续两年登上《脱口秀大会》的舞台,并成功拿下“大王”奖杯,成了“半个笑果人”。
实际上早在2019年,李诞就曾向周奇墨发出过邀请。那时候周奇墨已经是业内一致认同的“天花板选手”。可因为不是“明星”,每月只能靠给别人写段子挣钱,得到的报酬还不够养活自己。
那一次谈话,李诞和周奇墨说了很多,有关行业的变化、职业的规划,以及很现实的钱与名。周奇墨也认真思考了几天,最终还是选择放弃——当时他正在准备专场表演,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线上参加综艺节目。
等到《脱口秀大会》第二次找上门的时候,石介甫问周奇墨,这次想去吗?周奇墨回答,可以去试一试,“因为想给自己的段子找一个「好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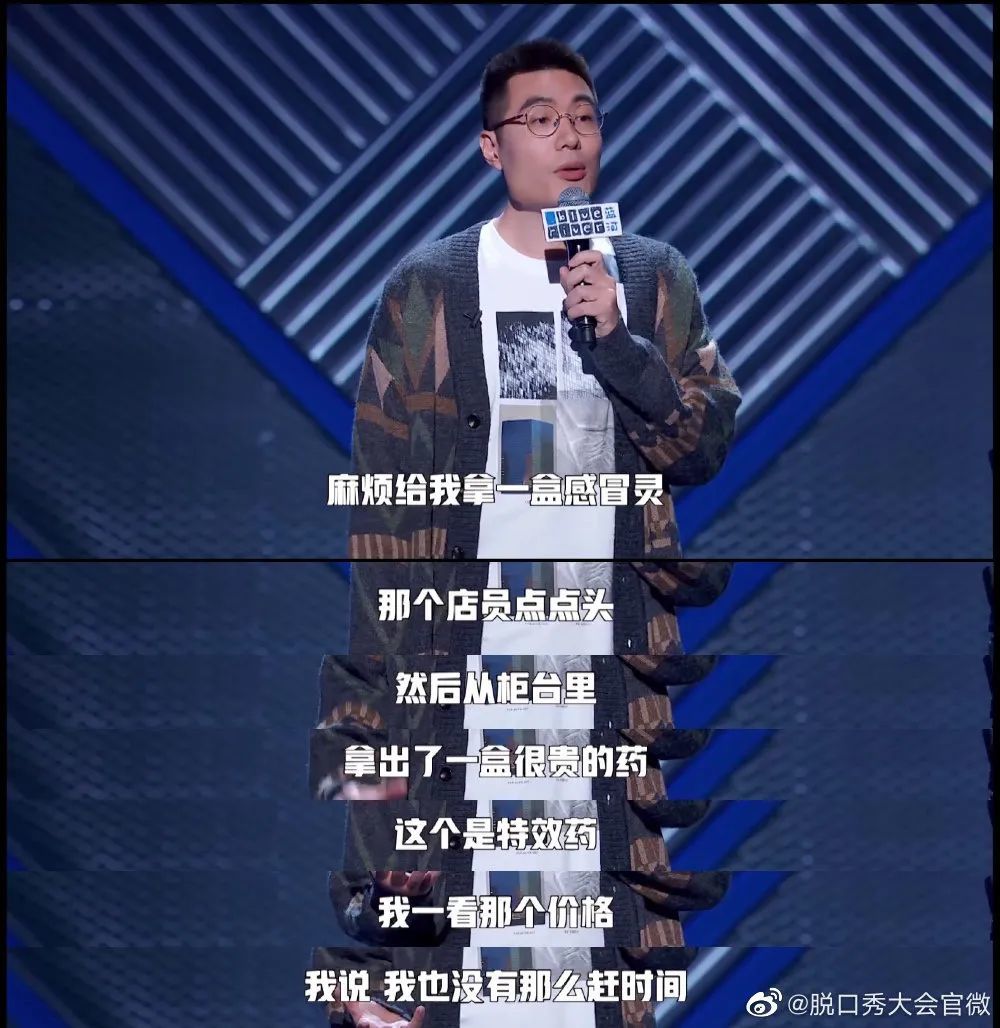
周奇墨参加《脱口秀大会》
线下开放麦和线上演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在线下只要每场观众不同,那同一个段子就可以讲无数次;换到线上,同样的段子绝对不能讲二遍,等到节目一播出,所有人都知道了。
就像是一场圣洁的超度仪式,线下可以“永生”的段子,在被搬上舞台的瞬间就成了“遗址”,可以重播,但不能重复。
参加《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时,周奇墨在选手内投环节中排名第一,但在节目正式播出时,他的表现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天花板不好笑”的争论伴随了他整季赛程。
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在脱口秀行业里,多数专注线下演出的演员,会将开一场60分钟的专场作为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但在互联网综艺中,观众期待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些“一秒炸场”的爆笑段子。
周奇墨用一年的时间适应线上节奏,终于在2021年,他拿下了《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年度总冠军,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份迟到的奖励。
节目播出后,周奇墨从北京搬去上海,和“笑果”建立了长期商务合作关系。他没有和“单立人”解约,可大家心知肚明,这个人一走,就很难回来了。
这是一场无法说出“背叛”和责怪的分别,毕竟在这个行业里,红与不红的区别是巨大的。
还是要主动争取点什么,不然生活就只剩下糟心的“被动”了。

周奇墨
海浪涌向北方,将一位优秀的渔夫冲进了南方海域。浪花带来了新人,也冲击了停靠在海的“笑果”巨轮。
《吐槽大会》至今已经播出五季,流量一路上涨,口碑却不断下滑。观众受够了尴尬的段子、多余的广告、刻意地洗白,一波接一波发表评论:节目还不如弹幕好笑。
让吐槽变尴尬的理由有很多。脱口秀是一个有关“冒犯”的艺术,但显而易见的是,内娱多数明星不接受“冒犯”。
在《吐槽大会》筹备阶段,说服明星上节目是最困难的环节。节目组几乎找遍了娱乐圈所有带有“槽点”的艺人,有的当场拒绝,有的则在沟通稿件尺度环节暴跳如雷:上来就揭短,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疯了?
极少数艺人接受真正的吐槽,整容、婚姻、前任、同行竞争……这些都是明星的“禁区”,他们不允许触碰的底线有很多,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好像只有“底线”,毫无上限。
周杰作为“主咖”的那期《吐槽大会》(现已下线),是节目上线至今收获好评最多的一期,“笑果”的编剧完成了对周杰和嘉宾的全方位调侃。正式录制前,导演组制定了十几种应急方案,大家都害怕周杰会翻脸,甚至想到,一旦艺人真的撂挑子跑了,就把他的电子照片摆到舞台上接着“吐”。
万幸,最糟糕的结果没有发生,周杰完成了整场录制,并靠“自黑”完成了一场口碑逆转。

周杰作为“主咖”参加《吐槽大会》片段
那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一些经纪公司开始主动推荐自家艺人录制《吐槽大会》。报名“主咖”的人越来越多,“冒犯”的边界却在不断收紧。当时“笑果”算上李诞、王建国也不过十几个编剧,每期节目要产出超过200个段子。好不容易稿子写完了,交给经纪人审核,几乎删掉了所有段子:我们是来“洗白”的,谁让你真吐槽了?
娱乐圈里没有“娱乐精神”,《吐槽大会》也就没有吐槽。为了扭转局面,节目在2021年全面改版,不想“吐槽”回来了,“大会”没有了——
在《吐槽大会第五季》体育专场下集因“剪辑时间不足”暂停播出后,这档节目也退出了大众视野。那期惹出“烦”的节目,也许大家都略有耳闻。无需多言,因为不让多言,总之,足篮打水一场空。
如今再看,这次“暂停”更像是对脱口秀行业的警告:球都不让吐槽了,你还吐槽个“球”?

范志毅参加《吐槽大会》片段

《吐槽大会》的消失静悄悄,却在行业内引起了巨大震荡。所有人都敏锐地接收到了那个讯号:
脱口秀,要小心。
2020年、2021年大概是脱口秀圈里最混乱的两年:
《今晚80后》编剧赖宝因突发疾病去世,王自健决定转行做一名演员,思文和程璐离婚,某池退群、某姆入狱……
也是在那段时间,一向不喜欢“管理”和“被管理”的李诞进入了“笑果”管理层。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来专业律师为公司全体员工、演员进行普法,并组织验尿。
李诞的警觉短暂地拯救了“笑果”,由他担任总策划的《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大获成功,提高了口碑,也突破了圈层。往后几年,节目稳定发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输送几段互联网“爆梗”。
那是全民都在讨论脱口秀的时候,也是脱口秀接受全民“审查”的阶段。
周奇墨曾说过,在线上说脱口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线上的观众好像不是来看段子的,是来审视你的”。
周奇墨曾说过一个关于京剧的段子,第二天视频流传到网上,立马就有京剧爱好者通过微博私信他,指责他侮辱国粹,还有人在视频下留言:“他不知道翻跟头的那些孩子们要流多少血。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就不懂得尊重和敬畏。”
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位网友都可以变成“判官”: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然后骂你。

周奇墨经典脱口秀段子“listen to 伯伯”
在中国的喜剧语境内,“冒犯”就等于“冒险”,又或者说等于“挨骂”。每一位脱口秀演员都要具备精准区分可以冒犯、适当冒犯和禁止冒犯的界限。
不要讨论“死亡”,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要调侃女性,否则就有“厌女”嫌疑;不要开伦理的玩笑,因为中国人极其看重三纲五常;拒绝把弱势群体当段子素材,那违背人性道德;宗教、神仙也不能取乐,举头三尺有神明,胡说八道遭雷劈……
讲到有关颜值、身材的段子,最好只针对自我调侃,否则就会被追问是不是在传递“容貌焦虑”——这种误解也许只会发生在女性群体,毕竟很少会有男人质疑自己的长相。

徐志胜
在中国,任何一场演出都需要经过批准,所有要讲的脱口秀段子文本都需要上报。严格的审查会让从业者了解“冒犯”的边界,红线之内,谨慎发言。
在线下开放麦演出时,只要不涉足“禁区”,舞台可以为所有讽刺免责。但到了线上,演员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个体上升到群体,火星点燃一排“雷点”,大战一触即发。
一个鲜活且典型的例子,就是杨笠的“普男”观点,就连她本人也无法预料,自己一句发自肺腑地提问能让男性集体“破防”。
当然,有争吵也是好事,至少证明那些说出的段子是有回响的,脱口秀演员更担心的其实是沉默。
一个梗抛出去,全场一片死寂,观众用迷茫的眼神看着你,真诚地问出一句“然后呢?”。
天啊,那一刻段子和演员一起死掉了。


杨笠
某期《今晚80后脱口秀》录制结束后,王自健接到了导演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节目需要补录,因为“段子不够”。王自健纳闷,100多个段子,一期节目足够了。导演又说,是审核过后能播出的段子不够。
相同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审查标准甚至越来越严苛。这是一个行业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是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规范不需要讨论,只需要服从,然后适者生存。
当“冒犯”的尺度不断变化,创作也需要随机应变,这就格外考验“人”的能力。
每一位脱口秀演员都经历过“憋稿”,坐在电脑前脑袋空空,不知道怎么开头,也不知道要写什么的经历,没人能一辈子靠“灵光乍现”的天赋写稿,脱口秀到最后都是“技术活”。
《今晚80后脱口秀》录到后面几季时,整个编剧团队都有种被“榨干”的感觉。没有那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了,大家都在机械地套用“公式”,以求得到一个安全的段子,至于好不好笑,不重要了。
《脱口秀大会》之后,大批脱口秀演员成为“明星卡司”,他们进入娱乐圈、登上综艺舞台,开始承接大量商务工作。留给脱口秀的时间被不断压缩,大家越来越忙,越来越有钱,但谁也没能再写出一个“满分段子”。
取得《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冠军后,周奇墨只参与了一场线下开放麦演出,谈到“成名”后的感受,他说:
“很多东西都透支了,对前路失去了很多憧憬,没什么劲儿了。”

周奇墨获得《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冠军
2022年,李诞卸任“笑果”董事,开始在娱乐圈活跃。再聊起“脱口秀”,他坦言,其实并没有那么热爱,过去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我就是活在浅薄里,大家都一个德行,最后都得死”。
没想到一语成谶。
2023年5月,“HOUSE事件”之后,“笑果文化”在上海、北京的演出全部停止,开始内部整改与自查、自纠。
此后,那些红极一时的脱口秀明星,近乎一夜消失——
他们都去哪儿了?以后还会说脱口秀吗?脱口秀综艺还能重回舞台吗?
答案,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李诞
2021年,米未传媒筹办《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单立人”作为“内容战略合作伙伴”参与其中,艺人编剧六兽、“少爷和我”中的刘波鑫仔被推向舞台。
“单立人”迈出了新的一步,石介甫说,这算是一次新的冒险,大家都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少爷和我”组合:张哲华(左)、“单立人”艺人 鑫仔(右)
巨轮一夜搁浅,黎明时分,太阳照常升起,海水依然蔚蓝。
风浪过后,海面恢复平静,又有新船启航,这一次海上没有“赢家”,只有求生者。














